- 科普文化
地域环境对中医学术流派发展的影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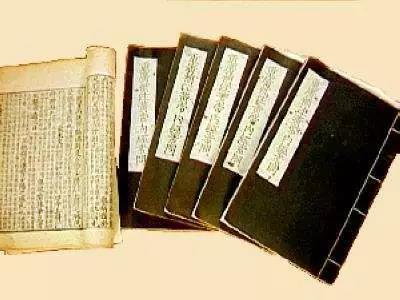
中医学数千年历史中呈现出一源多流的现象,奠基于四大经典中医学术主干,在后世发展分化为多个学术流派,使中医学术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。对于如何理解流派的差异及争鸣,人们众说纷纭。其实,不同流派的产生往往有其根由,明了其根源,对于评价流派才能有一个较为合理的角度。
从历史上看,中国幅员广大,各地区的气候环境有着较大的差异。南方以岭南闽粤为代表,闽粤地跨热带,蒸发甚而腠理疏,既易受寒,又易受湿,故多用燥药以化湿;北方以山西、陕西等地为代表,天气高寒干燥,冬季寒风凛冽,人体肌腠固密,故多用麻桂重剂发表。
很多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,其实与地域环境的差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一、《黄帝内经》奠定“因地制宜”的法则
中医学的运用应随地域环境而有所变化,这即中医“三因制宜”原则中的“因地制宜”。中医经典著作《黄帝内经》对此有典范性的论述,大致上有两种角度,即分别以阴阳与五行为基础。
从阴阳角度,《黄帝内经》具体以东南与西北为例讨论地域的阴阳盛衰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说:“天不足西北,故西北方阴也,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。地不满东南,故东南方阳也,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。帝曰:何以然?岐伯曰:东方阳也,阳者其精并于上,并于上,则上明而下虚,故使耳目聪明,而手足不便也。西方阴也,阴者其精并于下,并于下,则下盛而上虚,故其耳目不聪明,而手足便也。
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中也有类似经文,并谈到两地人群体质与寿命的区别说:“高下之理,地势使然也。崇高则阴气治之,污下则阳气治之,阳胜者先天,阴胜者后天,此地理之常,生化之道也。……高者其气寿,下者其气夭。”
时而还论述了地域对疾病机理及治疗大法的影响:“岐伯曰:西北之气散而寒之,东南之气收而温之,所谓同病异治也。故曰:气寒气凉,治以寒凉,行水渍之。气温气热,治以温热,强其内守。必同其气,可使平也。假者反之。”
从五行五方角度,《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记载得更为细致,如说:
“东方之域……鱼盐之地,海滨傍水,其民吃鱼,而嗜咸……其病皆为痛疡,其治宜砭石……”“西方者,金玉之域,砂石之处……其民华食而脂肥……其病生于内,其治宜毒药……”“北方者……其地高陵居,风寒冰冽,其民乐野处而乳食,脏寒生满病,其治宜灸焫……”“南方者……其地下,水土弱,雾露之所聚也,其民嗜酸而食胕,其病挛痹,其治宜微针……”“中央者,其地平以湿,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,其民食杂而不劳,故其病多痿厥寒热,其治宜导引按蹻。”
这里不仅说明了由于各地的地形、水文、气候等地理条件的不同,使得各地居民有不同的生活习惯,而且还分析了由于环境和生活习惯的不同,往往还影响到人体的健康状况,因而会产生不同的疾病,同时也需要不同的方法,因地制宜予以治疗,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。
二、两晋至金代对地域医疗经验的因循渐积
后世医家在《黄帝内经》基础上,对地理环境对临床治疗的影响有一些更为具体的论述。
如六朝陈延之《小品方》指出:“凡用诸方欲随土地所宜者。俱是治一冷病,共方用温药分两多者,宜江西、江北;用温药分两少者,宜江东、岭南也。所以方有同说而异药者,皆此之类也。”
唐代《千金方》说:“凡用药,皆随土地之所宜:江南、岭表,其地暑湿热,肌肤薄脆,腠理开疏,用药轻省;关中、河北,土地刚燥,其人皮肤坚硬,腠理闭实,用药重复。”
《外台秘要》也曾谈及应用灸法时注意到南方气候炎热的特点,在“灸用火善恶补泻法”中讨论“灸不过三分”时,指出“若江南岭南寒气既少,当二分为准”。
不难看到,晋唐乃至宋代,对地域环境的影响大多局限于用药法则、治疗分量等具体的差异上,逐步积累起较为表浅经验。同时在这一时期,中医学术模式中也没有什么流派之说。及至金代刘河间、张从正、李东垣三家崛起,创立新说,后世为之命名为寒凉派、攻下派及补土派,他们的思想主要受宋代理学纷争的影响,以及缘于对运气学说的反思,同时他们与晋唐大多数医家一样,主要居于北地,学术中对地域问题并无太多讨论。
三、南方地域促使中医学术带来变革
宋室南渡后,江南经济文化日益繁盛,在此背景下,学术水平较高的医家渐次增多,其中当其冲者即浙江的朱丹溪。
他在融前人学术之长的基础上,大力赞扬金代三家的创新,但又鲜明地指出不同。其立论的基础,相当强调地域区别。如在讨论李东垣升阳益气之法时说:“西北之人阳气易于降,东南之人阴火易于升,苟不知此,而徒守其法,则气之降者固可愈,而于其升者亦从而用之,吾恐反增其病。”
由朱丹溪开始,江南名医辈出,他们可以说沿袭朱丹溪注重地域差异的角度,使中医学术面貌出现较大变化。
这里以温病学说的产生为例进行讨论。众所周知温病学派诞生于明清时期,但其源头实可溯源于朱丹溪。《丹溪心法》论外感说:“《内经》云:邪之所凑,其气必虚。内伤者极多,外感间或有之,有感冒等轻症,不可便认为伤寒妄治……西北二方,极寒肃杀之地,故外伤甚多;东南二方,温和之地,外伤极少,所谓千百而一二者也。”
这里所说“外伤”即指寒邪所伤,认为在南方较为少见。随后即有元末王履(江苏昆山人)鲜明地提出“温病不得混称伤寒”,开启了新的发展方向。及至明末清初,经过5 位江南医家(江苏吴县吴又可、叶桂、薛生白,江苏淮阴吴鞠通,浙江杭州王孟英)的努力,确立了温病学说,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形成分野。
其实,自《伤寒论》以来,历代医书并非不言温病,无论是《诸病源候论》《千金方》还是《伤寒总病论》《圣济总录》等,都设有专篇,但何以始终未深入发展下去从而突破伤寒体系呢?
笔者认为并非后世纷争中所说前人因循守旧、识力不够等等,重要的原因是在长江以北地域里,此类疾病的发病数量以及典型性都不足够,北地医家虽加重视,但尚未具备条件提出新说。像《备急千金要方》所说:“其伤于四时之气,皆能为病,而以伤寒为毒者,以其最为杀疠之气也。即病者,名曰伤寒;不即病者,其寒毒藏于肌骨中,至春变为温病。”相较之下觉得温病危害并没有那么重要。
《伤寒总病论》开始将“天行温病”作为专节,但所列的病名如青筋牵、赤脉、白气狸、黑骨温、黄肉随等,实际源自《千金方》的五脏阴阳毒,其病名颇为怪异,似只是套用五脏五色理论模式,而非来自充分实践基础上的经验总结。
至江南医家崛起,他们在常年接触的大量病例中,积累了诸多与北方医家不一样的实践经验,也历经了二三百年之久的酝酿,始形成卫气营血辨证、三焦辨证等温病辨证体系。
其实江南医家早期也尝试改良伤寒体系来治疗温病,最有名的是明代陶节庵(浙江余杭人),其《伤寒六书》,认为“若言四时俱是正伤寒者,非也。此三者,皆用辛凉之剂以解之。若将冬时正伤寒之药通治之,定杀人矣。辛凉者,羌活冲和汤是也”。
其所创羌活冲和汤一方号称为“以代桂枝、麻黄、青龙、各半等汤”的神药,又有柴葛解肌汤等名方,然而他既被伤寒家批评“其六经分证,牵入《内经》热病法与仲景伤寒法,一并砌入,混同无别”,以致被视为“仲景罪人”,又被后世温病家批评说“盖温病误表,纵不成死候,亦必不易愈矣,麻黄、桂枝,人犹胆怯,最误人者陶节庵之柴葛解肌汤也”,两不讨好。由此可见,温病学说脱离伤寒而独立,在当时实有其必要性。
寒温分立,一直引来许多争论,但持平之论者,多能从地域角度进行讨论,如清代新安医家程钟龄说:“东南之地,不比西北,隆冬开花,少霜雪,人禀常弱,腠理空疏,凡用汗药,只须对症,不必过重。予尝治伤寒初起,专用香苏散加荆、防、川芎、秦艽、蔓荆等药,一剂愈,甚则两服,无有不安。而麻黄峻剂,数十年来,不上两余。
可见地土不同,用药迥别。”并针对麻黄汤指出:“此方不宜于东南,多宜于西北。西北禀浓,风气刚劲,必须此药开发,乃可疏通,实为冬令正伤寒之的剂。若东南则不可轻用,体虚脉弱者受之,恐有汗多亡阳之虑。”
当然这不等于说南方地域诞生的学说就只能适用于南方,王孟英在《温热经纬》中评陈平伯《外感温病篇》“独是西北风高土燥,风寒之为病居多”一语时指出:“亦不尽然。”他不但认同陈氏“而凡大江以南,病温多而病寒少”的意见,更进一步指出“北省温病亦多于伤寒”,“投以发表不远热,攻里不远寒诸法,以致死亡接踵也”。反之亦然,南方也并非不能用伤寒法,具体全在于辨证而已。
《黄帝内经》所确立的“因地制宜”原则,随着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变迁而不断得到充实。在晋唐以前,中国经济文化的重点在黄河流域一带,对疾病的医疗经验以北方为主。随着宋元以降经济文化重心向东南转移,对南方的地理气候及医药特点的认识逐步加深,推动了明清温病等学派的形成,促使中医学术发生明显变化。
以前对这种变化有许多争论,其实从地域角度来看,这些变化是因客观条件而促成,并非某些医家的“标新立异”或“背古”。参考现代临床科研的概念,可以说地域条件的差别越大,气候条件和病证特征越典型,同时可供观察的病人样本数量越大,就越有利于理论与治法的创新。而这种创新,当然不可能用于否定其他典型地域诞生的理论,它们都可以并存于中医学术框架之中,从而带来中医学术的深化,这也最好地说明了中医基本理论的包容性和可扩性。
同时,基于地理环境、四时气候、人群体质以及临床疾病的多样性,虽然各个学说诞生的地域不同,但它们在所有地域都是有其应用价值的,只是如果从“大数据”来看,各地应用的情况有多有少,范围有广有狭而已,这就在总体上表现为不同地区的医药特色异同,成为地域医学流派分立的依据。

